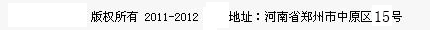这是关于鱼山饭宽(曾仁臻)的第二篇访谈,第一篇访谈详见:为每个人造一座园林
除了游园,曾仁臻还大量的游山,他在山里看到了园林,看到了佛道的世界,也看到了建筑的构成,从来没有一个现代人这么游山!
行李曾仁臻
1.
行李:你曾经说过,画家们在描绘名山大川的时候,比画一些普通的山川还是要更生动一些。
曾仁臻:名山大川大家会经常谈起,如果去过的话会发现,有些山的特点的确已经被经营出来了。比如说一线天,还有那种悬了一块石头的,甚至还有摩崖石刻,大家都已经赞美过了。它是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所以在绘画的时候也会注重去刻画,相对准确,同时人在里面的活动会进行相应的描述。看这种画能看得进去,比其他山水画那种囫囵一个山的程式化表达肯定要生动。
行李:哪一座名山的山水画比较具有代表性?
曾仁臻:比如黄山就很多人画。大家对于黄山山水的了解实际稍微晚一点,但黄山这个名字其实很早就有,可能秦汉时就知道有这样一座山。但真正被文人去记录宣传,包括画家去画,大概从明代才慢慢开始,因为明代中后期才有僧人去开山道,去山上建一些房子,有个普门和尚去做这个事儿,后来徐霞客也去爬过,但他爬天都峰的时候还没有修通山道到峰顶,还挺危险的。
另一个就是有些当地画家、僧侣对它更为熟悉,像梅清、弘仁,还有石涛。石涛去过黄山三次,每次去待一个多月,对黄山有比较多的观察和了解,他画的黄山有自己的特色,都云雾缭绕,云把山遮了一块,截了一段,甚至会在云里点一些若隐若现的小人。这的确也是黄山最大的特色——云海,在所有山水里黄山最像仙山,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接近于道家仙山的山水。
▲曾仁臻系列画作之“山”,《游山品山图册》节选。在每一座山里,步道,都是其中很重要的构成。
行李:所以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曾仁臻:去华山之前我也觉得黄山最好,我很喜欢现代人在黄山修的前山道,当然有些地方修得也不是太讲究,但整个布置是非常好的,用园林的方式来讲,就是“曲折尽致”。我最喜欢天都峰,徐霞客当年天都峰还上不去,一直到后来有僧人把天都峰的路修上去了,才真的很棒。
行李:天都峰如何好了?
曾仁臻:现在黄山的游客一般是从后山坐缆车上去,然后绕到天都峰,大家一般都不去爬天都峰,因为那块儿有点险,也许是因为管理上不方便,所以设计给大多数游客的线路是先让人走一大圈,最后看到天都峰都不想爬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从前山上的,因为主路人太多,登天都峰选择了僻静些的前山道,后来发现前山道是年代才修的,当初修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流游客形成登山环路,但这里是一个次要路线,所以山道不宽且比较险。
我查过一些资料,当时黄山管理局提了一个要求:时间上要20个月修建好;所有的道路要集中在风景集中的地方,这就意味着要做大量勘察去设计路径和停留点;还有,树大于二十公分的不能砍,你在一个本来就很陡的地方凿山道,遇到树还得绕着走,而且还要走得舒适,这是非常难的,得动脑子。当时的开发条件不如现在,更多的是依赖传统的开山方式,人过去凿。你会发现很多崖壁上,或者很陡峭的岩石上,旁边的栏杆是用凿台阶凿出来的石块直接做的,所以石头不规整,不像现在很多栏杆是切出来的,整整齐齐,当时只能就地取材,取一块补一块,和自然很融合,当然我现在是猜测。
还有一些崖壁山会凿出嵌道,本来这块岩石没路了,我在里面凿出一个嵌道,留出一个有台阶的槽,让你能看看外面的景,这种地方也比较特别。
还有的地方会在一些起伏的岩石上起桥,过不去,那我就顺着山势的高低,在几块大岩石之间起桥,看上去,桥就是路,不算桥,看上去又像桥,非常美妙,就是造型和山势是呼应的,如果按现在很多人用的粗暴的方式,可能就是把石头削平了,要么就是在高一点的地方加一个铁栏杆过去。我觉得这样不见得是省事,也难看,你看黄山这样就觉得也巧,也省事,特别符合山水的形。
在山顶上,会利用一些大的岩石凿刻出大沙发,沙发后面一排树,后面再有一块岩石,可以变成榻,就像室内一样,把室内家具的关系布置进去了。
行李:这一段听起来好迷人,感觉这些工头就是当代的室内设计师。
曾仁臻:把自然描绘成室内,中国的山水画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尤其是那天有点下雨,看不见十米以外的东西,因为你看不见更远处,就觉得在园子里,白色的云墙在你身外,有些东西时隐时现,外面的景观就这样被“借”进来了。
我喜欢天都峰就是因为它很像园林,我喜欢园林也是因为它和山水的关系。中国人处理园林也好,处理山水也好,都是在处理一个事情:人如何生活在自然里,或者和自然生活在一起。当代西方建筑处理和自然的关系,许多都是开特别大特别干净的玻璃,对着一颗树,其实身体还是隔开的,当然这是一种方式,但中国人的方式是把内外交织在一起,把它请进来,把自己弄出去。园林里的人在屋里坐着,看看外面的东西,觉得那边很好玩儿,就出去转一转,再回到屋里坐一坐……而日本的枯山水是不让人进的,只是坐着静观冥想,另外,中国人还要讲看的好坏,窗户如何开,开在哪个位置?是方的,还是六边形、月洞形?都要讲看的姿态,看到景色的俗与优,要再次做选择。所以爬天都峰可能会理解中国人在没有园林之前对待自然的态度。
行李: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描述黄山。
曾仁臻:我今年会新出一本书,是《幻园》系列的第二辑,叫《借天工》,以前我们常讲“巧夺天工”,现在提起“夺”似乎就意味着人太霸道了。我觉得现代人面对自然改造经营必须首先要学会人工与自然的平衡,弄清楚理景的判断价值在哪里。“借”也助于我们重新反思园林里根本性的问题,《园冶》里最重要的就是借景,为什么园林要重复的谈“借”这个事情?为什么西方的造园不谈借?我爬了那么多山,看了那么多山道,悬桥和山里的房子,发现人在大山里是多么渺小,但还要在一个山水里面建房子!可是你不建造经营又何以达成你山水居游的愿望呢?因为人力的渺小,“借”天然而作,达到事半功倍,就出现了一套智慧和审美的东西,借着借着可能就变成一种有智慧的审美了。
你看自然里的东西,无论是栈道还是房屋,你都发现非常舒服,不突兀,因为我们固有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最后成为了审美,影响了造园,变成了我们栖居文化里一个核心的东西,“借”来自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这个现实问题我们现在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现在有技术,有钱,有人力,这也导致核心价值的崩溃,所以有这么一层源于现实的价值的缺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恢复,我只是陈述这个价值可能是这么来的,《园冶》是世界最早的造园著作,谈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借”,如果我们后面再谈建筑,谈园林,都离不开这个事情。
行李:如此说来,黄山应该是你最喜欢的山呀。
曾仁臻:但我对黄山特别不满的是天都峰之外的其他山道,因为要满足大量游客的涌入,有些山道已经凿得过宽过直,缺少转折和明暗变化,游和停的关系不太好,甚至开口炸石,也许本来一线天的地方,开一个大的豁口,破坏了山本身应该有的节奏和自然天趣。游山是需要节奏的,必须有的地方险一点,有的地方放松一点。
行李:节奏感是通过步道来体现的。
曾仁臻:游是非常重要的,逛园子也是在游,一定是劳逸结合的,不能一直很舒服,也不能一直很累,要有节奏感,身体是起伏变化的。这方面华山做得非常好,我现在可以说,我最喜欢的山是华山,单独论山峰的话,最喜欢黄山天都峰。
▲云海中的天都峰,因为步道的合理设计,游山就像游园林。
2.
行李:那来聊聊华山吧,我看你最近就登了华山。
曾仁臻:华山早在《山海经》里就有描述了。最早说它是整块岩石,劈成了四方的。四面都比较陡峭。它一直以来都是五岳之一。西岳、中岳,这几个岳一直没变,北岳和南岳都有过变化。北岳曾经是河北的大茂山,后来才变成山西浑源的恒山。南岳以前也变过,但主要还是指衡阳的衡山。封禅最多的就是西岳、东岳和中岳。像西岳华山,我认为是五岳甚至是中国所有山里整体评价最好的。如果只论自然风景,黄山可能要稍微好一点,但华山也不逊色,它有它的特点。然后从人文方面、山水改造方面、建筑遗迹方面考量,华山应该是最好的。它的改造时间最长,也非常有特点,奇、险。
▲华山俯瞰。正对我们的是南峰的大岩壁,著名攀岩家何川曾沿着画面中左右两条线路分别攀岩过。东、西、北峰就在中央这块大石山的其余方向,华山景观因为比较集中,就像一个微缩的盆景,如此可见一斑。摄影/秦小平
行李:改造时间最长是什么意思?
曾仁臻:因为华山一直处在政治中心的附近,离西安很近,离洛阳也不远,所以历代一直有文人去爬它。它改造得非常多,比如山道。通常考察一个山水,会很明确地意识到,山道各有特点,差异非常大,尤其是跟改造时间有很大的关联性。华山的改造历史至少有两千年,至唐代已经修通至主峰顶,也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山道的修建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因为不同年代的人会不断根据它的地形地貌去改造,一点点改,选择能看到更好风景更适合攀爬的地方改造。我们现在看有些山,开发得比较晚,或者新近开的,就发现走路是没问题,但总觉得景色没那么好,或者是走起来很累,或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这说明一个问题,山道的修建是需要时间沉淀下来的选择。
比如华山的苍龙岭,那就是在一个峰刃上的一条小道,韩愈爬苍龙岭的时候不就吓得投书了吗?现在那条道改宽改深,一般人爬已经没有什么危险。还包括一线天处的千尺幢,都是很高很陡峭的台阶,这是经过历代人的改造选择,它沉淀下来的东西是没法用技术简单代替的。现在修一条索道上去多简单,但可能很乏味。华山应该算所有山里山道修得最好的。黄山的天都峰在年代也修过前山道,修得也挺好,它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修,没有大量依赖机械,而是用石头一块块来凿,也非常漂亮,并选择出了最好的观景路线。
▲华山步道,在曾仁臻看来,步道才是华山的核心价值
行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好像从来没想过登山的路径对风景的作用。
曾仁臻:对,很重要。可以说一个道理,中国山水画通常有几个重要的标准要遵循,就是可行、可望、可居、可游,这是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里明确提出的。山水改造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标准去评价,大部分的山是可以望的,百分之二三十是可以行的,但可游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除了走路能上去,还要在适当的位置停一下看风景。华山除了行,还有游,哪怕险一点,但上去突然发现脚下就是一块悬空的石头,一览众山小。
可居就是山上哪怕有个石穴或者有个洞窟,人可以在里面过夜或住在里面生活,华山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它是一座道教的山,其他的山可能佛教多一些。道教有一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极致理解,首先他们会选择风景很好、超然脱俗的环境修行,另外他们也吃得了苦,可以风餐露宿,哪怕辟谷不吃东西,反正他们可以在华山那种很难生存的地方生存下去,真的像神仙一样。所以他们走的路、住的地方,都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人也很难到达。所以形成了一个居住的特点,这特点非常完整,从山道到居住方式——石窟,元代贺志真就在华山开凿了很多石窟,包括南峰主峰上,他在崖壁上开凿了一个长空栈道,过了栈道才到他修行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开凿栈道就是想远离人世,最开始他开凿得没那么险,但后来他肯定是想更清净,越修越险,最后修到那么一个地方去了。现在就变成一个收费的旅游景点,大家要是想去尝试一下那个栈道,是需要再交一次钱的。
▲华山上的道教场所,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教的影响,这些步道绝不会这么开凿。
行李:华山路径的绝险在国内再也想不到第二个了。
曾仁臻:华山以前更险。现在那些以前太险的地方就凿宽了一点。比如苍龙岭,以前就是石背上的一些小台阶,基本上人真的要靠爬才能上去,现在把它凿深了,也宽了,就没有那么险了,就是险而不危。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像千尺幢。现在从旁侧又修了一条缓路。不过我去的时候,听当地人讲,他们觉得现在这种山道的修建破坏了华山原有的神秘感。并不是说每个山都要所有人都上去,真想上去可以坐索道,我看到那些后修的山道也确实非常乏味,完全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人能走。没有游,也不巧,修得很直接很笨拙。所以这个确实对华山在某些方面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讨论的,倒不一定说它肯定是错的,人当然都想去山上试试爬爬,看看风景,但度要把握好。如果我们要把华山看成一个文物,这个文物是不是每个人都得看见,每个人都需要去摸一下,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华山是一个盆景式的山,很精致,很集中,所有的文物古迹、山道很集中,它不是一个能承受大规模、一天几十万游客流量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到节假日的时候,游客堵在山上下不来,导致以后景点可能会修更多的措施,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行李:其实不只是华山,所有这些好地方都是跟旅游业冲突挺大的。
曾仁臻:因为旅游业的目的是为了商业,不是为了保护山水文化,这个现在就是有点开发过度了。倒不是开发本身有问题,而是经营管理的方式和规模的控制。
行李:你刚才提到道教与山水的关系,中国的好山水多少都与道教有关吗?
曾仁臻:对。中国的三教,儒道释,土生土长的道教是融合了老庄、玄学、方术等一些东西形成的。我认为中国人真正的美学,比较高级的,还要算道家美学。我们最欣赏的还是道家神仙般的生活,就是山水间那种飘飘渺渺。所以在美学上,对山水的改造上,像道家为主的华山,确实代表了一种极致。佛家在这方面是向道家靠近的,吸收了很多道家的美学思想。中国的寺庙环境是尽量结合山水,当然最开始也是因为修行本身也需要建在比较偏远的山里。道家也一样。但从理解自然的态度,它不是简单的自然主义。我去西藏的青朴就觉得特有意思,在桑耶寺附近,他们其实对当地山林没什么改造,无非就是住在洞穴里,人和动物是和谐共处的,经常能看到野鸡、飞禽走兽什么的,那就是佛家秉着一种对自然的态度,就是和谐共处也不伤害山林。这是一种可能无法称之为美学的东西。但道家是从中衍生出美学了,无论从诗歌文学还是绘画上,它就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它一定要天人合一。它不是像青朴那样,山就是山,人就是人,我也不去过多干预你,但中国人是要改造山水的,改造完以后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工”,还是一个共处的方式。所以这里面会衍生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包括用自然做的器物,比如木头、竹子等等。不是说不改造,而是基于一种态度去改造。所以从美学上讲,道家或道教对于中国山水文化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比如中国真正的山水诗歌,从贵族到下层,山水美学慢慢进入到民间可能是从魏晋,就是玄学兴盛的时候开始的,竹林七贤,开创田园诗山水诗的陶渊明、谢灵运,到隋唐以后三教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融合的过程,同时也使山水改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明初洪武年间,精于诗画的医学家王履在游历西岳华山之后,绘制了《华山图》四十开,与诗文序跋合为一册,蔚为大观。曾仁臻出于喜爱,用自己的方式模仿了一套《华山图册》,请注意人在其中的痕迹。
3.
行李:说说你的绘画吧,很多人都是从你的作品开始认识你的,太有有趣了。感觉把传统与现代无缝连接在一起。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的创作灵感?
曾仁臻:其实主要还是在思考传统文化如何继承的问题,能不能有新的生命力,产生新的创造力。无论是绘画还是建筑,我认为都是创造力的问题,并不是说古代的就不能继承,而是如何继承。在继承之前肯定还是得熟悉,传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练不练是一回事儿,你知不知道是另一回事儿。我为什么要大量的看山水,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在园艺上支持我。画画也是这样,比如造园,古人造园之前也要熟悉山水画,这都是他们认识事物、感受事物的方式。里面的美学到底是什么?有些东西可能解释不清楚,但你一定要去感受,这是一个前提。既要往后看,也得往前看。一直往后看会固步自封,但你只往前看,只看未来,没有历史观,可能就意味着判断事物的格局上就比较小,视野也比较窄。得到前面的智慧和教训,再想想以后会怎么做。学习古代的东西,创作园林、山水画,包括看诗歌文献,都是学习传统的一部分。包括我第一个阶段的绘画,主要是从传统山水画里重新去认识山水画。
行李:最开始的创作还没有人物出现?
曾仁臻:相对少些。最开始的画还是主要寻找山水画里最有价值的东西,去找山水画里我认为好的、局部的环境。因为山水画通常除了大的、程式化的框架,也有些小的精彩的局部环境,包括山水环境和建筑环境。所以要从中挑选,再重新去经营一个类似的空间,是这样一个学习的方法。这个就是在学古人。
以后做建筑,更重要的肯定还是要理解现代人的生活和认识事物的方式。但古代的东西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要在实践中检验。比如现在和古代,人们看待山水的方式就不一样。古代人没有这样便利的交通,古代的山水也不是圈起来收票的。古代人一进山可能就半个月吃住在山里,现在的人基本一天就游完,有时候我也是一天游完,因为门票死贵,还有时限,不能待太久,人流也太大。看山也从生活、体验的方式变成一种游赏。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都在变,造园子是,山水画也是。如果从纯粹画山水的角度,我会很强调山水画入画体验的问题,人到底愿不愿意进去,是否有入画居游的愿望。这也是我做建筑要考虑的。如果现代人有这样的愿望,那就对了,实际上就不分古今了。
▲曾仁臻的“幻园”,就是园子或私宅的设计图。
行李:所以你画的那些小人实际上是想牵引着大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