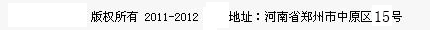年,林散之(左)与邵子退
一位是20世纪誉满中外的书法大家林散之,一位是一生蛰居乡间的“种瓜老人”邵子退,但他们怀有同样的家国情怀,并在一生中通过诗画唱和。
他们一同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等跌宕起伏的时代,到最后,留下声誉的是书画大家,留下声音的则是乡间布衣。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布衣的孙子邵川经过30多年的追寻,让自己身边这段传奇故事变得清晰,也更加懂得了爷爷们的诗和远方。一位是20世纪誉满中外的书法大家林散之,一位是一生蛰居乡间的“种瓜老人”邵子退,但他们怀有同样的家国情怀,并在一生中通过诗画唱和。他们一同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等跌宕起伏的时代,到最后,留下声誉的是书画大家,留下声音的则是乡间布衣。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布衣的孙子邵川经过30多年的追寻,让自己身边这段传奇故事变得清晰,也更加懂得了爷爷们的诗和远方。
仅是4月中旬,安徽和县粮食局的退休干部邵川就往南京浦口区的林散之故居跑了3趟。
其中一趟是参加央视纪录片《百年巨匠·书法篇》开机仪式,纪录片拍摄对象是启功、赵朴初等6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邵川的“林爷爷”林散之是其中之一。另一趟则是给林散之故居新建成的展室,送自己爷爷邵子退的照片。
“他现在要是说起林散之,可以三天三夜不停口。”邵川的爱人对丈夫的这种热情早已见怪不怪。
而多年前,这个安徽人对眼前两位老人的传奇故事,竟然毫无意识。
事情好像是从诗集出版后,就变得奇妙了起来。在县粮食局工作的邵川没想到,突然之间,“元白”、“苏黄”、“伯牙子期”这些他听都听不懂的赞叹,从著名学者冯其庸、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等人的笔下写出,接连朝着他那在乡间布衣一生的爷爷涌来。
最奇特的一次,他陪爱人在南京看病,邻床的病友和他们寒暄:“你们是和县人?你们县出过‘种瓜老人’邵子退哎!”
“那是我爷爷。”邵川很纳闷,“你们咋知道他呢?”
对方笑了:“叶兆言的书里写过呀!”
“我初次接触到关于邵子退的文字时,就好像读到了一些神话故事。”江苏籍作家叶兆言在文章里说,“在我看来,六朝人物早就是过去,早成为无法模仿的历史,但是邵子退的故事,似乎正在说明,……古迹仍然可以追寻,时光仍然可以倒流。”
“乖乖,这么厉害?”邵川如获至宝地读了又读,就好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邵子退生前在乌江“种瓜憩庐”
可那是自己认识的爷爷吗?
从邵川有印象起,爷爷总是沉默地待在老家乌江镇的小砖房里。他长年穿着陈旧的布衫,偶尔出门帮林场修剪桃枝。每天干完活,他会在房里看看书、写写字。总之,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头”。
至于他在涂画什么,家里也没人关心。
直到爷爷去世。
直到远方的赞美纷至沓来,这位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年人才较起了真:究竟爷爷的一生,经历过什么?
这份好奇心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再怎么看,也只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头”
邵川从没问过爷爷“您的一生是怎样的”,尽管他身为长孙,从小就在爷爷身边长大。
从他记事起,一家人就住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那年头,镇上还铺着青石板,弯弯曲曲的街道由南至北,两旁是店铺,人流熙熙攘攘。一条河穿镇而过,河对岸还是乌江镇,却已经属于江苏南京。
爷爷邵光晋,字子退,号种瓜老人。大多数时候,他闭门谢客,在家过着安静的生活。除了有几年,乌江街道办了一个林场,邵子退被请去帮忙管理——上世纪50年代时,他被下放回乡,就干过看守桃园的活儿,有经验。至于爷爷为什么会被下放,邵川到现在也不知道。
总之,除了很多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不知道”外,一切都普通极了。
只是,河的另一边,也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林散之。
两位老人隔三差五就串门,一块儿打打太极、练练书画。林老耳朵不好,说话特别大声,但和邵子退在一块儿,两人不说话,只以笔代口,互相写纸条,“几乎没得声音”。两个一身破衣服的老头儿就这样聊天,还常常能讨论到夜半。
邵川从没想过去了解一下两位老人聊什么。
又有谁会在意呢?
再怎么看,也只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头”。
那正是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邵川上学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我家里没受啥冲击”,他说。只是,课堂上也再没什么要下苦功的学问,邵川印象最深的课程内容是军训,出门拉练,大家伙儿“天天玩得快活”。不军训时,同学们会兴奋地上街“看批斗”,“亲眼看着多少书被烧掉了”。
他的世界,与爷爷邵子退“格格不入”。
“爷爷常跟我说,你把《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读熟百篇,在社会上就能立足。”想起往事,他笑着摇头,“我哪里听得进去,当时社会上都在说读书无用论。”
很多时候,从学校兴冲冲地跑回家时,少年邵川会在三间砖房前的场院上见到正与爷爷一块儿打太极的林散之。
显然,这两位老爷爷是一个世界的。
他们聊天、写字、绘画。
林散之爱画,他原本退休后在南京书画院工作,“文革”开始了才回到老家来。他常常拿起邵子退的画作,添几笔点染,然后一块儿讨论哪儿添得好、哪儿画得精彩。有一回,有人就拿着这么一副邵子退亲笔画、林散之加工的山水,约上两位老人一块儿聚在林家的书房里,瞅准了二老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问:“诗堂谁题?”
“我题!”林散之抢过了这一任务,沾饱墨,在纸上写下“画中有诗”几个汉隶大字。
年,林散之与邵川笔谈
比起自己作画,邵子退更喜欢在一边看林散之泼墨挥洒。这让林老急得抱怨他“一天到晚看看看,自己也不勤于练习”。
邵川也喜欢不时去凑热闹,涂上一两笔——不管怎么说,毛笔字能用来写大字报,还挺有用。看见“小和世孙”(邵川乳名小和)有兴趣,“聋爷爷”也很乐于提供指点,告诉他,该去临什么碑帖。
现在想起来,已经两鬓斑白的“小和”说:“如今是没有这样的朋友了。”
一年冬天,下着大雪,邵川陪爷爷在河对岸林散之家里作客。眼看天色将暮,林老琢磨着应该没有其他人会再上门了,就把爷孙俩带进书房,说,“我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他取出了一本黄宾虹真迹的画册。
“真有点古人说的‘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意思。”邵川说。
那是年,别说什么《古文观止》,邵家连《辞源》这样的传统工具书都已经给烧了。因为家里有人参加过远征军,是“战犯”,所以一点“四旧”都不敢留。
这是邵川第一次见到黄宾虹的画,“墨色很干净,很饱满,只有磨出来的墨,才有这种质感,”他至今都记忆犹新。除了“墨色光亮”,画中山水还“笔笔中锋勾勒”。他觉得大开眼界。
他后来才知道,很多年前,黄宾虹曾专门为邵子退画过山水。就连邵家的楹联,也是出自黄的手笔。
怀抱谁同誓,唯君无间然
如今,邵川还是常常回到当年爷爷与林散之彻夜长谈的地方。4月中旬,位于南京浦口区乌江镇的林散之故居一片繁忙,包括林散之长子林筱之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纪录片摄制组而忙碌着。在“书法篇”中,摄制组选择了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林散之,作为上个世纪中国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
在挂着“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匾的江上草堂门外,邵川笑嘻嘻地指指右手第一间屋:“我就是在那里看到黄宾虹画册的。”
林筱之带着他参观刚改建好的故居。不一会儿,邵川就在现场的陈设中发现了问题。
“这两张画的顺序放反了哎”,他对正忙着整修故居的乡亲说,“还有里面那个人物介绍,张敬夫,名字写错了,应该是另外那个‘章’,‘立早章’!”
前来拜访的人一拨又一拨地涌向林筱之,邵川很快就落了单。
邵川19岁那年,林散之意外出了名。
他记得林老拿着一本杂志上家里来串门,告诉他们:“《人民中国》登了我的字。”这是日文杂志《人民中国》年的1月号,在那期包罗了中国不少名家的“书法特辑”杂志上,林散之的草书“东方欲晓”被单独列在首位。
因为纪录片开拍,南京市浦口区委宣传部特意在他们的官方乌鲁木齐治疗白癜风医院安徽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