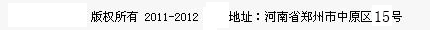南方周末报道以前在黄山市,“徽州”还是敏感词。年,《人民日报》发表《可惜从此无徽州》时,黄山市政府还曾致函人民日报报社,说文章“在社会上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观点也是有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黄山发展的批复和要求的”。
“徽州复名实际上就是一场新的改革行为。哪有改革没有成本的呢?”
多年来,在安徽黄山市,路牌被迫打上了许多括号:黄山市(屯溪)、黄山区(太平)和黄山风景区。对游客而言,黄山风景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山。不得已,旅行社将三者的区别写进了“游客须知”。
这一切的尴尬,都源自年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当时确定了这三个基本相同的地名,黄山市、黄山区和黄山风景区,其中黄山市是代指整个地级市的范围,而黄山区则特指以前的太平县地区。
其实,黄山市并非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年前的年间,作为州府名,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过。
近千年的命名戛然而止,转眼已经近三十年了。这期间,要求黄山复名徽州的呼声从未间断。近一个月来,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徽州复名的讨论进入了另一个高潮。
更多的博弈在改名之外,山之南与山之北,同一座黄山,不同的方向。
“割地”成就的小黄山市
年夏,邓小平同志在安徽省委第—书记万里陪同下视察了黄山,后来发表了被认为拉开了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大幕的“黄山讲话”。
讲话中,邓小平对陪同的安徽省委及徽州地委领导提出要求,“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为了落实邓小平指示,安徽省委立即在黄山召开常委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措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把原隶属于安徽省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管辖的黄山管理处,改为安徽省黄山管理局,直属省人民政府领导。
黄山管理局的成立给黄山旅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这种体制机制能调配的资源依旧有限”,黄山管理局原副局长崔之康说,比如每年的旅游旺季,随时需要大量的季节性临时工,按规定用工要有计划,经过审批方可使用。
在计划经济年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拿游客的餐饮来说,粮、油、肉、蛋、豆制品以及燃料都要有计划,否则就没有供应,“但黄山可不能让游客带着粮票来旅游。况且,外省粮票到安徽不管用,只有全国粮票才通行”。
省政府为此曾多次召集省直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只能解决一时,却解决不了长久”。
至今,崔之康仍记得,当时黄山底下汤口镇的粮站负责人曾不无调侃地说:“别说黄山风景区现在升格归省里管,即使将来再升格归北京管,吃粮食还是要我供应,给他吃细粮粗粮、新粮陈粮我说了算。”
黄山管理局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平方公里,山下大门以外就无权管理了,“黄山风景名胜区成了一座’孤岛’”。
最后,省政府决定,将黄山风景名胜区与原隶属徽州地区(今黄山市)的太平县全县,加上歙县的黄山公社、石台县的广阳公社划在一起,合并成立县级黄山市,上报国务院。年12月1日,国务院发文批准同意,于是直属省政府管辖的县级黄山市(后来的小黄山市)就正式宣告成立了。
崔之康以黄山管理局副局长的身份,兼任第一任市长,“黄山管理局是正局级机构,而黄山市只是正县级机构”,但是崔之康却更愿意去山底下任职,因为“可以真正做一些事情”。
不过,“小黄山市”是行政指令下的产物,有先天缺陷。根据国务院规定,设立县级市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市区人口,二是工业产值。当时这两个条件黄山都没有达到,只是由于黄山旅游资源在全国风景名胜区中的特殊地位而特批的。
小黄山市的成立,开了一个先河,即由一个省属地级事业单位管辖县级地方政府的先例,并引发了以后大、小黄山市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
大小黄山之争
“小黄山市当时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铁路”,据原安徽省旅游局局长张脉贤回忆称,小黄山市当时的交通、经济、人口等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太好,对黄山旅游发展提供的助力有限。
年6月9日,在当时的安徽省徽州地委书记胡云龙的主持下,中共徽州地委、徽州地区行署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黄山管理体制设立徽州市的报告》。
报告中指出,现行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徽州、黄山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黄山历来隶属徽州,解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属省、地双重领导,黄山旅游业的发展有赖于徽州经济的发展,黄山的自然景观需要徽州的人文景观来衬托,徽州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离不开黄山。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无论徽州地方志还是宣州地方志都记载为‘黄山当宣歙二郡’。所以,徽州觉得划出黄山公社给小黄山市如有割让‘国土’之痛。”崔少康说。
徽州地区当初并不希望太平县与歙县汤口等地分给小黄山市。于是在年向省上以及国务院提交申请,要求撤地设市,并要求将“小”黄山市并入其中。
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安徽省调整徽州地区行政区划的批复》,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地级黄山市。原属徽州地区的石台县划属池州地区,绩溪、旌德2县划属宣城地区。
年4月,徽州地区撤销建制,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小黄山市”并入黄山市,并改名为“黄山区”,原属于徽州地区的绩溪被划出。
对于将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当时其实有过讨论。黄山市成立之后,张脉贤从安徽省旅游局局长调至黄山市担任市委副书记。据他了解,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意起名为“黄山市”而不是徽州市,这和时代环境有关。
在现已退休的崔之康看来,今天在徽州改名讨论中,“一些媒体朋友和文化界朋友批评不用徽州名称是没有文化的愚蠢表现,是失之公允的,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当时的社会状态”。
比起改掉徽州的名字,真正让张脉贤遗憾的是,把原徽州地区重要属县绩溪县划归宣城地区管辖。这在当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张脉贤曾陪着当时的徽州地委书记胡云龙去北京协调过此事。当时中央有关领导考虑到徽州作为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地级市,而且又是帮扶对象,经济体量太小,担心带动不了那么多县城,因此就把绩溪划出去了。而且当时中央领导也提过,“这种行政划分只是暂时的,过段时间根据实际情况,仍旧可以调整”。
据崔之康回忆,年徽州改为黄山市之后,总体分为两种反应:一种是徽州以及支持徽州成立黄山市的群体表示拥护,因为徽州成立黄山市意味着收回黄山,有“收复旧山河”的喜悦。当时根本没人想到,这样会把徽州这个文化载体也消灭了。
同时,黄山景区、小黄山市干群都表示反对。因为黄山景区和小市过去直属省政府管辖,现在降为市级管理,他们当然有意见,认为“这是一场地方政治博弈的结果”。
“哪有改革没有成本呢”
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之后,关于复名徽州的呼吁浪潮,二十八年间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对徽州文化的认同感,在近15年里进入了爆发期。
年,黄山市有了第一个网络论坛故园徽州。胡卫东是它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名80后,年少时他对徽州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直到后来去外地上大学,不断地从别人嘴里听到徽州两字,才意识到自己徽州人的身份,并对徽州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批类似胡卫东这样的年轻人在网上聚集,最后创办了这个网络论坛,分享徽州文化的历史资料以及进行讨论,复名徽州也成为论坛上隔三差五就冒出来的议题。
青年学者吴子桐是北大政治学博士,和胡卫东的经历类似。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徽州就是一张邮戳,小时候对这张邮票有印象,但是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直到去外地上学,关于徽州文化的意识才逐渐在脑海中觉醒。
媒体讨论也在助力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早在年,人民日报知名记者、作家李辉就在《人民日报》上刊载过一篇《可惜从此无徽州》的报道,批评年将徽州易名为黄山市后,导致“皖南处处皆黄山”,外地游客“到了黄山不见山”;而且,历史悠久的徽州被名山大川“吃掉”。之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教育家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呼吁恢复徽州的致信,曾掀起过一阵讨论。
荆州和沙市合并改名为“荆沙市”,襄阳和樊城合并改名为“襄樊市”之后,李辉都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批评,并最终见证了这两个地区恢复曾用名,“荆沙市”最后改为荆州,“襄樊市”最终改为襄阳市。但是在徽州改名的呼吁中,李辉却感觉“为何这么难?”
今年4月13日,李辉再度在《人民日报》刊发《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一文,引爆了本轮关于徽州复名的大讨论。讨论中,李辉也注意到了有不少人讨论徽州改名的成本问题,他认为愿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应由当地人来决定,“最终是否决定改名,应该由当地人大会议、政协讨论决定”。
他认为,过去的更名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如今就是要更正过去的错误。另外,在关于城市更名成本的讨论中,他并没有看到相关的报告,所以也很难确定这些更名成本是怎么统计得来的
崔之康也支持更名,他认为:“徽州复名实际上就是一场新的改革行为。哪有改革没有成本的呢?”黄山是我国发展旅游业的第一波改革试点,三十几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的黄山需要的是转型。
徽州籍政治学者吴子桐多年来也一直在 成本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陈政近些年感觉,无论是公务员群体,还是普通老百姓,大家对徽州文化都有强烈的认同感,也都支持徽州复名。他说,复名不是简单恢复名称,应该是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域范围对现区划进行调整,比如绩溪的回归。
但问题关键在于大小黄山市之间的争论,“如果说复名后,要将黄山分割出去,那么还不如不复名。”陈政说。
张脉贤观察到,在要求复名徽州的声音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纯粹为了出于对徽州文化的认同,希望把黄山市的名字改为徽州。还有一种声音是要借徽州复名,把黄山从徽州地区“独立”出去,“如果是这样,将对徽州旅游造成巨大损害”。
事实上,崔之康感觉合并多年后,整个黄山市仍旧有“重南轻北”的感觉,所谓南即是指原属于徽州地区的“一府六县”。黄山区并不是过去徽州的“一府六县”,合并之后,有人感觉黄山市对整个黄山区仍旧缺乏信任。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项目里,黄山区只占很少比例,江西婺源和绩溪占很大比例,理由是黄山区不是徽州的原来一府六县。“还有一点让人无法理解,合肥至福州高铁,位于黄山南边的黄山站,站台写着‘黄山北站’。其实从地理位置上讲,小黄山市在黄山之北,这是误导游客,也使黄山北面的人感觉很不爽。”崔之康说。
与民间热火朝天的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回应。吴子桐曾协助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起草过关于复名的提案,有关部委回复的大意是,时机并不合适。
在人民网安徽省省长的留言板上,也有网友在年提出过复名徽州的请愿。黄山市民政局回复称,“黄山建市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级黄山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黄山市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是符合黄山经济社会发展的,也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我们认为目前不宜进行区划和管理体制的调整”。
据吴子桐回忆,以前在黄山市,“徽州”还是一个敏感词。有一次他向当地的党报投了一篇关于徽州的稿子,“结果有好心人怕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还把稿子要了回来”。直到最近15年,徽州才逐渐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年,李辉在《人民日报》发表《可惜从此无徽州》以及陶行知夫人的回信时,黄山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还曾致函人民日报报社,说李辉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观点也是有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黄山发展的批复和要求的”。
18年后,官方的态度正在松动。年4月13日李辉再度在《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一文,呼吁徽州复名。与18年前的致信斥责不同,黄山市很快便作出了积极回应。
4月14日,黄山市民政局局长朱学军就此接受了人民网采访,称更改市级名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民政部门,将深入调研,尽早提出建议。
赞赏